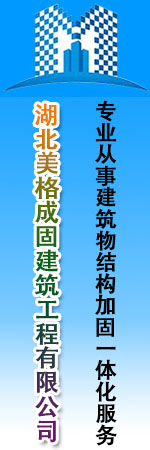9名工人都嫌多,馬義和決定把工人減少到5人。
7月19日,在上海青浦區(qū)滿是近半人高野草的園區(qū)里,石子路被太陽曬得滾燙,上海盈創(chuàng)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馬義和戴著安全帽走在前面。他皮膚黝黑,這是時常守在工地的結果。他計劃要在這里建4幢小高層樓房,其中一幢已初具規(guī)模。
與普通工地不一樣的是,這里沒有堆放的建材,工人們也不需要在現場砌筑。工地旁邊,是一個被白色巨幕圍擋起來的大型廠棚,里面才是真正干活的家伙——一臺有半個籃球場大小的3D打印機器。
“28日,我們就在建好的這幢樓里舉行發(fā)布會,給大家身臨其境地感受3D打印房子!”馬義和語氣堅定。
100多公里外的烏鎮(zhèn)西柵景區(qū),另一個工地上,也有兩臺機器人。它們在為建造新一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場館助力。承建者是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(guī)劃學院教授袁烽的團隊。他設計的機器人并不僅僅做3D打印,還展開了機器人木構、磚構等多種實驗性建造實踐。
兩個工地本沒有交集,但在國家對智能建筑的引導下以及工業(yè)4.0來臨之際,卻有著相近的意義。兩者都是上海企業(yè)及科研團隊介入建筑業(yè)轉型升級的嘗試——機器替換工人,成為“機器匠人”。
為了突破勞動力短缺以及傳統建筑行業(yè)工作環(huán)境差等瓶頸,全球建筑界把目光投向智能建造領域。袁烽認為,中國建筑業(yè)機器換人的拐點正在到來。
拐點
7月28日,遠離城區(qū)的青浦區(qū)新金路,平時難見一輛車的小路兩旁停滿了車。長龍綿延數百米,其中不乏豪車身影。
進入會場,找座位很難;幾百人的會場還設置了同聲傳譯的工作間,現場有來自非洲、歐洲、中東、南亞等的出席者。
這場面與5年前那場發(fā)布會的情形,不相上下。
2014年就在這個園區(qū)內,盈創(chuàng)在24小時內打印出了10幢灰色矮房,宣稱是全球第一次用3D打印技術造出供人居住的建筑。
“以前都是我到國外去(學習),后來是一車一車的外國人到我這里參觀。”馬義和說,公司在蘇州工業(yè)園區(qū)接待了數以千計的參觀者。因為需求過于旺盛,他按人頭收費,一人300元,參觀費就收了幾十萬元,“全部用于科研”。
即使如今,坐在人群當中,依然可以感受到人們對3D打印技術的追逐。到場者里有產業(yè)上下游的廠家,有結構工程師,還有高校負責人。一所上海高校計劃開設建筑專業(yè),希望把3D打印作為亮點。
但記者同時也能感受到不少人依然對此概念模糊。一位出席者戲謔地形容:“知道它好,又不知道它好在哪里。”
在過去的5年,3D打印建筑始終進入不了主流。馬義和想不通。
他做建筑材料起家,1993年在老家湖北襄陽創(chuàng)業(yè)。據他介紹,原先建造房屋需要先制作模板再澆灌水泥,而現在的3D打印技術模板用量及鋼筋綁扎的工作量大大減少,縮短一半以上工期,降低50%-80%人工;此外,油墨(即混凝土材料)原料是改造后的建筑垃圾、工業(yè)垃圾、礦山尾礦,還能省下30%至60%的建材。
2015年1月,盈創(chuàng)宣布打印出了全球最高的3D打印建筑“6層樓居住房”和全球首個帶內裝、外裝一體化的1100平方米精裝別墅。通過與海外設計公司Gensler合作打印迪拜辦公樓項目,盈創(chuàng)還成為全國第一家在海外運用3D打印建筑技術打印辦公樓項目的企業(yè)。
放眼全國,北京、廣東等地近年來也正在進行類似探索——將人工智能等創(chuàng)新成果運用于建筑領域,讓機器真正滲透進工地各生產環(huán)節(jié),讓人成為管理者,進而將中國制造推向智能化。
袁烽提供了一組數據:業(yè)內有個共識,當一個地區(qū)的建筑工程中勞動力成本占建筑成本總額比例超過35%時,會出現“機器換人”。在發(fā)達地區(qū),比如中國香港,這個數字已超50%;在內地,這個數字多在30%以下,而上海略為特殊,這個數字剛過33%。
多數勞動力成本高的地區(qū),主要采用預制建筑構件、推廣裝配式建筑發(fā)展的方式。上海此前也緊跟步伐,市里規(guī)定2016年起外環(huán)線以內新建民用建筑應全部采用裝配式建筑;外環(huán)線以外不少于50%,并逐年增加。
彎道超車?中國并非沒有可能。
機器
與馬義和認為3D打印“全是優(yōu)點,找不出一個缺點”的情感有著極大不同,袁烽很少使用3D打印的標簽來描述自己的工作。3D打印技術,更專業(yè)的說法應為“增材制造”,指通過逐層增加材料的方式將數字模型制造成三維實體物件的過程。“但機器智能建造也可以做減材,比如機器人可以銑削加工木材。”
袁烽的看法是,3D打印建筑最重要的意義是機器換人,但3D打印并非機器換人的唯一方式。他更傾向于解釋自己的領域是數字化設計與智能建造,即通過算法實現機器比人更為精準和節(jié)能的建造。
7月26日,烏鎮(zhèn)的工地上,最高氣溫直逼40攝氏度。工人們每天下午不得不等到3時多才能開工。
但兩臺會砌磚的機器人不受影響:每天工作16個小時,工期緊張時,24小時也不成問題。
相比普通工人,這兩名“工人”無疑擁有整個工地最好的工作環(huán)境——獨立工棚、地面干凈,還有電風扇散熱。
只見機器人用手臂抓磚、抹漿、砌墻,動作一氣呵成,砌到邊緣部分,還會聰明地只抹半邊砂漿。機器人砌出的墻面也不一般,每塊磚的角度不一,最終形成波浪般的視覺效果。
“機器適合做漸變的非線性梯度變化。一般人砌磚間隔都是一致的,但是機器砌出來的,單獨看一片看不出什么,組合到一起就能看到韻律感。”袁烽指著波浪般的墻面說。
十年前,他也運用數字化軟件設計過一面擁有綢緞般流動肌理的“綢墻”,但當時沒有機器人,全部使用定制模具和人工砌筑完成。他記得那面不算大的墻,砌了兩個月之久。而這次,長40多米、高2米多的復雜墻體,兩周就可完工。
距離驗收時間只剩一個多月,施工方有些著急,袁烽則沉著許多:“兩臺機器相當于以前兩個班組,差不多二三十人,但現在(機器之外)只需要四個人,人的勞動強度大大減少。”
和記者每說起一個作品,袁烽總會報出建造時間——上海思南書局里的書報亭,從策劃到建成用了21天;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場館中近9000平方米面積,100天完成施工……
2008年,袁烽去麻省理工學院當了一年訪問學者,其間選擇了數字化設計與建造方向,歸來后就專心于此。他初中學過編程,拿過全市競賽一等獎,但上大學后沒再繼續(xù),直到去了麻省理工,才發(fā)現“人家是學科之間互相打通”,于是將編程重新撿起。
從2011年研發(fā)出第一代建筑業(yè)機器人開始,袁烽團隊已研究8年之久,其中移動現場式機器人已經更新到第5代,可以完成3D打印、砌磚、銑削、彎折金屬、切割石塊等12項工藝。
在上海徐匯西岸一個項目中砌再生磚墻時,他們甚至給機器裝上“眼睛”,讓機器判斷磚的大小以及放置的位置。
烏鎮(zhèn)工地上來自上海的項目經理姜濱,在這行干了10來年,但機器人做出來的造型,他從未見過。
據國際機器人聯盟(IFR)的統計,2017年中國機器人需求增長速度達到58%之高,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機器人銷往中國。中國正逐漸成為世界最大工業(yè)機器人市場。
掣肘
顧慮并非沒有。
馬義和快被“標準”的問題問膩了。7月28日的發(fā)布會現場,依然有人追問相關問題。
3D打印建筑目前沒有專業(yè)規(guī)范,在設計建造時只能參考相近的結構和外觀建筑標準,并通過實驗設計來確保其結構等方面的安全可靠。
“創(chuàng)新的東西哪里有標準呢?都按標準的話,還會有創(chuàng)新嗎?”馬義和大聲說。
話是不錯。但涉及到人住的房子,哪一方都不敢怠慢。
發(fā)布會上,葉蓓紅發(fā)言時,起身拍幻燈片的人明顯增多。翻頁快時,還有人互相叮囑:“都拍下來了嗎?”
葉蓓紅是上海建筑科學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,其發(fā)言題目為“3D打印材料(油墨)及3D打印產品標準研究”。
“所有人都在關注標準的問題。”葉蓓紅介紹,國家標準體系分為政府標準、團體標準、企業(yè)標準。
2017年,住房和城鄉(xiāng)建設部發(fā)布過一個關于工程建設標準體制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見稿,明確提到:“經合同約定,團體和企業(yè)標準可作為設計、施工、驗收依據。”
這條方案的提出給盈創(chuàng)這樣的企業(yè)發(fā)展找到了突破口。背后是政府釋放的善意——“既要體現政府的監(jiān)管要求,又要滿足設計施工等單位的需求;既要確保管住管好,做到‘兜底線、?;?rsquo;,又不能管多管死,限制企業(yè)創(chuàng)新。”
基于此,葉蓓紅團隊目前已對盈創(chuàng)的油墨強度,墻體材料抗震、抗凍、放射性、防火等方面做出了企業(yè)標準,并在國家質量技術監(jiān)督局網站上備案。下一步的目標是制定協會標準,這需要更多企業(yè)參與。
葉蓓紅的發(fā)言博得了持久掌聲。但仍舊有人質疑,“3D打印建筑的安全性因素除了材料、墻體,還有建造結構。結構怎么檢測呢?”
還有人說,盈創(chuàng)當前打印的更多為基礎設施,說明結構還是短板,因為結構需要大量復雜的算法驗證。
“數字建造的難點并不在現場,而在前期設計。”袁烽說,最難的部分就是生成形式、計算優(yōu)化、驗證。結構設計師的任務就是對結構負責,出了圖、簽了名字,如果出問題會被吊銷執(zhí)照,這是行業(yè)規(guī)則。
但在新興領域,確實有一些容易被忽視的因素。
前年8月,一座外表黝黑、以全新改性塑料打印的實驗作品步行橋成為同濟大學校園一景。42天之后,橋卻塌了。
“我們最初只關注到它可以承載多少人,卻忽視了溫度帶來的改變。”袁烽說,“當時有位材料學教授提醒我注意它在極端溫度下的表現。”果不其然,持續(xù)多日高溫后,變形導致壓力產生,最終橋塌了。袁烽據此寫了一篇報告在國際會議上發(fā)表。
此次烏鎮(zhèn)項目難度最大的是智慧亭,智慧亭的最終效果是一個非線性殼狀結構,這個形狀在學術上叫作“自由重力拱結構”,力不是垂直傳遞,而是完全軸向傳遞。袁烽團隊曾做過一個六分之一大小的殼體,這次雖然只是變了尺寸,但結構邏輯全都要變。
負責智慧亭項目的博士后王祥介紹,智慧亭的現場建造過程和搭積木很像。塑料模板先在工廠用3D打印技術預制好,運到現場后,工人拼裝、用螺栓固定。然后,在模板上鋪設三層薄磚,最后撤掉現有鋼架支撐。
但問題接踵而來。比如,機器3D打印出來的構件存在誤差,盡管在工廠經過預拼裝,但到了現場,還是有部位無法契合。工人們必須先用鋼構腳手架把結構架高,等表面磚結構成型再撤走。
異形建筑,工程驗收也是難題。袁烽打算邀請上海和浙江兩地的專家到烏鎮(zhèn)現場開會論證,盡管這方面的專家很少。
到時候,現場會采用堆載的方法,用沙袋把殼體堆滿。“均布式它是不怕的,所以我們會讓它一半負荷,以及最不利點集中堆載,驗證最不利的條件,還會做材料檢驗等。”袁烽很有信心。
機器與人
智能建造以后,需要什么樣的人?
應是兩種人:一類是操作機器的人,一類是設計機器工具的人。
記者曾在青浦觀摩了一次打印過程:90后楊慶(化名)當天16時30分就完成了那天所有建筑構件的打印工作。機械專業(yè)大專畢業(yè)的他到盈創(chuàng)工作至今,一開始還感到新奇,現在已經習慣。他甚至可以在空閑時打手機游戲,“打印太快的話,工人來不及裝”。
人們可以將打印過程想象成做蛋糕,噴頭就像裱花袋,調配的混凝土“油墨”就像奶油,根據設定路徑,一層層堆疊。
“工作環(huán)境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了。”一位工人說,工作強度也低了很多,只需要把搬來的構件“扶一下,往那一擱就結束了”。
袁烽說起去貴州參與扶貧時的感受:“現在的工地,40歲以下的工人很少。新一代年輕人,即使家里條件不好,下工地也是不肯的。”
在烏鎮(zhèn)工地上,22歲的操作工張運(化名)大專畢業(yè),學的是機電一體化,從未砌過墻,只用兩個星期就學會了操作這臺機器人。
包括建筑機器人在內的現今大多數工業(yè)機器人,都是一種可編程機器,通常只能被編程為執(zhí)行重復的一系列運動。但要真正代替一線工人,建筑機器人遇到的復雜挑戰(zhàn),并非僅僅實現“速度”或者“效率”就大功告成。
對于設計機器人的人,袁烽還是感覺缺人,“一般學設計的做不來”。
今年7月,袁烽在上海做了一個關于數字建造算法的匯報,聽眾幾乎都是建筑行業(yè)專家,最后不少人的反饋是“聽不懂”。
機器人建造早已開始跨界:建筑學、結構學、機械學、材料學、人工智能……以前,同濟建筑系學生是基本不需要編程的。而今,袁烽帶的碩士生周軼凡,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寫程序、調試機器人。
“建筑學是偏美學與人文的教育,要會畫畫、做手工、做模型、做設計。而編程是代碼,是純理性的。我們把兩者混合,就引出一個全新的建筑數字未來。”袁烽說。
比如砌磚機器人,除了運用建筑設計知識,還涉及到自動化、機械、電氣等專業(yè)知識。其核心功能都是袁烽和學生們琢磨出來的。直到原型機做出后,袁烽才找了機械和自動化專業(yè)的朋友幫忙進行專業(yè)提升。
“用機器代替人工,不單單是把人減掉,而是把新的人工用在計算賦能上。智能化時代,生產的所有東西都可以有微差。比如我們3D打印的構件,每個都不一樣,砌的墻面、每個磚頭的位置都不一樣,這是自動化程序做不了的。”袁烽說,機器人加入建筑業(yè)的意義,還在于提升建筑的性能和美感。
有多少智能建造,就意味著背后有多少“人”的參與。
盡管發(fā)布會開得紅火,但值得注意的是,發(fā)布會所在的樓房并沒有實現馬義和9天前期待的“完工”。
馬義和解釋:包工頭對3D打印技術認知不統一,停工3天,等他回來拍板時,已經無論如何趕不上了。
最終他們只完成了一樓的布置,3D打印了進門一小塊的水磨石地面,供參觀者“感受一下”。
或許這也意味著,機器再如何智能,沒有“人”的參與,也終究不過是機器